吉隆坡的晨雾裹着椰糖般的甜腻,宣礼声穿透502宿舍发霉的窗帘时,我正盯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照片。画面里青瓷盘盛着金黄的油香,浮在特有的粗瓷碗沿的羊汤热气,在像素颗粒间蒸腾成故乡的形状。
手机显示凌晨五点十七分。热带暴雨刚在铁皮屋檐奏完安可曲,空调外机滴落的水珠正敲打生锈的防盗网。我咽下第三口矿泉水,喉结滚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封斋时刻的饥饿像条狡猾的蛇,从胃袋游进记忆褶皱——去年此时,我该是就着破晓的鸽哨,把阿妈手作的烫面油香掰成月牙状。
"马同学?"混合着咖啡香气的英语从门缝渗入,房东陈太太的塑胶拖鞋在走廊啪嗒作响,"雨停了,要赶早课的话..."尾音融化在电梯井传来的金属摩擦声里。我抓过人类学概论课本,封面勒庞的《乌合之众》书名被圆珠笔划掉,改成了"孤独者的田野"。
八点零七分的人文学院阶梯教室,冷气出风口悬着的马来纱笼轻轻摇晃。哈桑教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同心圆:"甘榜(kampung)的竹楼结构,就是马来文化的物质隐喻——看似开放的高脚屋,实则有看不见的屏障。"我的笔尖在笔记本洇开墨迹,忽然想起兰州拉面馆的玻璃橱窗,那些氤氲水汽后若隐若现的阿拉伯文招牌。
"远哲!"台湾室友阿杰用课本碰我手肘,他T恤上印着褪色的摇滚乐队logo,"等下带你去十五碑吃椰浆饭?"我摇摇头,喉间干渴随秒针跳动逐渐具象化。窗外凤凰木的阴影爬过讲台,将哈桑教授的影子拉长成宣礼塔的形状。
图书馆冷气开得近乎暴烈。我在人类学书架区逡巡,指尖拂过《东南亚峇峇娘惹文化考》烫金书脊时,突然听见织物摩擦的窸窣声。转头看见戴浅杏色头巾的女生正踮脚取《红溪河人类学报告》,她手腕上的银镯滑落至肘部,在顶灯下划出新月般的弧光。
"需要帮忙吗?"话出口才想起该说马来语。她转头时头巾垂下的流苏扫过《斋月中的爪哇市场》扉页,杏仁状的眼睛让我想起西吉滩清真寺彩窗上的郁金香纹样。
"谢谢,我是阿米拉。"她接过书时露出虎牙,"你就是新来的中国穆斯林?"她的普通话带着马来语特有的黏连感,像淋了椰浆的麻糬。我们坐在落地窗边的木纹长桌,她翻开笔记本,露出里面工整的爪夷文批注,我瞥见自己潦草的中文笔记里夹着半张高考成绩单。
暮色将玻璃幕墙染成封斋时刻的深蓝时,阿米拉忽然说:"你知道吗?十五碑印度神庙的钟声和中央市场清真寺的唤拜,会在雨季形成特殊的声波共振。"她指尖轻叩桌面,"就像人类学的意义,在看似冲突的褶皱里寻找共鸣。"
我在渐暗的天光中摸到书包里硬挺的信封,那是今早在宿舍信箱发现的云南家书。父亲用经堂语写就的"尔林"(知识)二字洇透了劣质信纸,油墨在湿热空气里晕染成吉兰丹州皮影戏的轮廓。
暴雨再度倾盆时,我们被困在商学院廊檐下。阿米拉从帆布包掏出用香蕉叶包裹的椰丝球,掰开时拉出银丝般的糖浆:"开斋吧,安拉的慈悯在异乡人的分享中降临。"远处印度裔保安正在檐角点燃驱蚊香,檀木气息混着雨水的腥甜,让我突然明白哈桑教授说的"文化褶皱"——原来不同文明的肌理,总会在某个潮湿的切口处,绽放出相似的纹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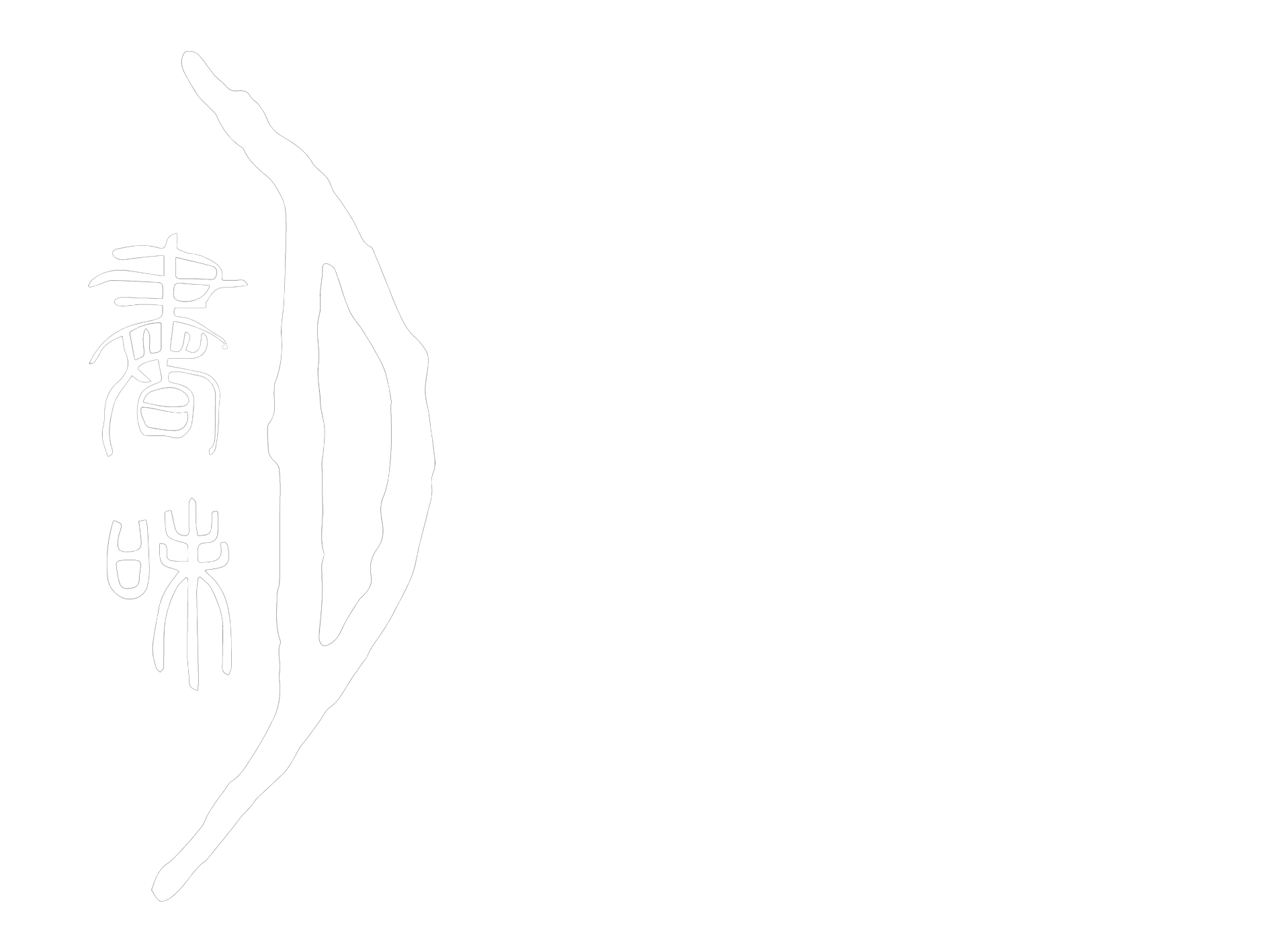
暂无评论
来做第一个评论的人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