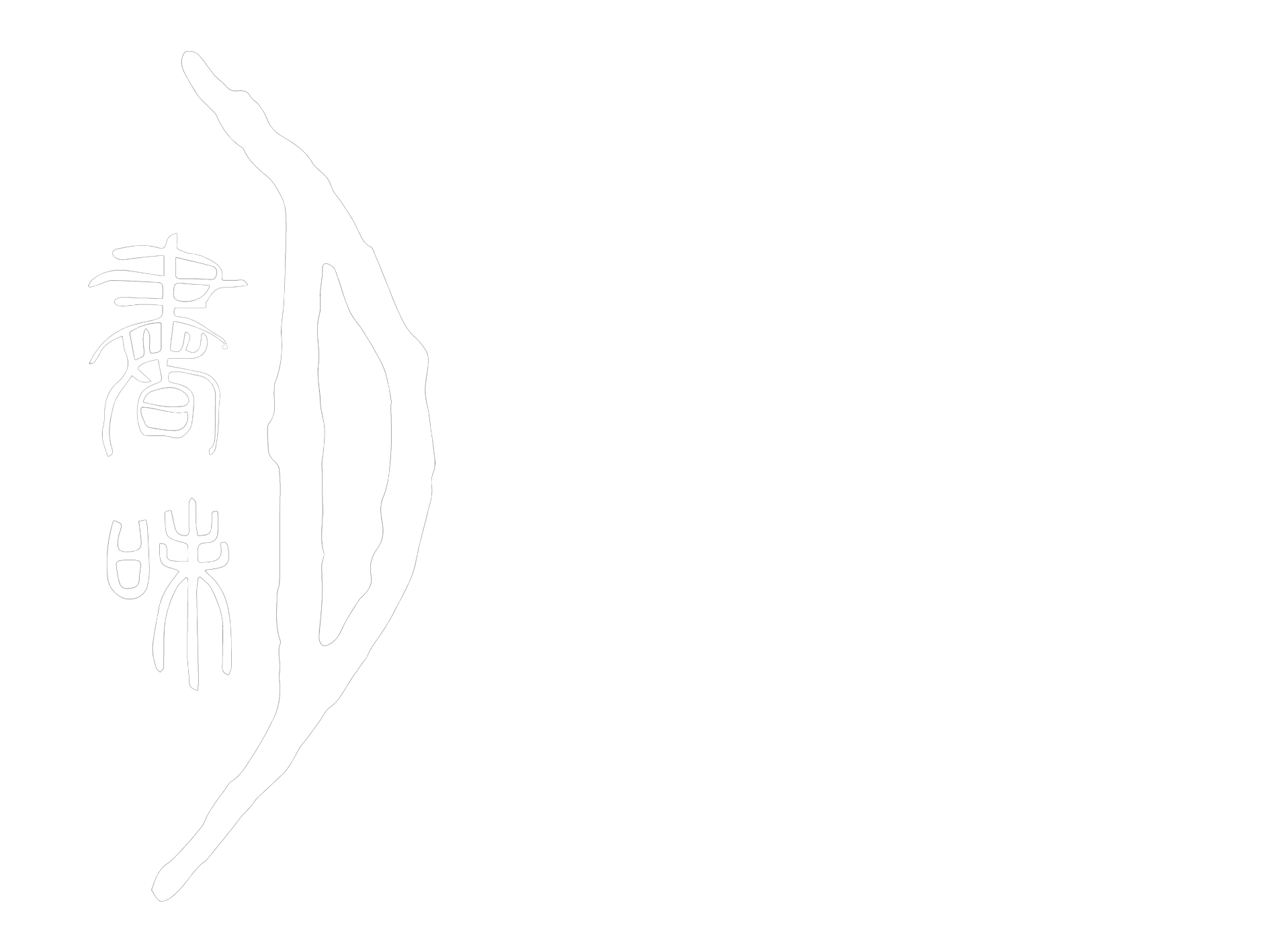标签 星盘 - 巴格达 - 医学 - 政治 - 萨利姆-阿尔-哈桑尼 - 女性 - 妇女
注:首次发表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的《穆斯林遗产》,2020 年 2 月 11 日,为“国际科学界妇女和女孩日”再次发表。
***
目录
1. 导言
2. 历史学中的妇女: 方法论问题
3. 近期学术研究
3.1. Muhaddithat 项目
3.2. 妇女词典
4. 概况
5. 医疗保健
5.1. Rufayda al-Aslamiyyah
5.2. Al-Shifa bint Abduallah
5.3. Nusayba bint Harith al-Ansari
5.4. 15 世纪土耳其的女外科医生
6. 数学
6.1. 苏泰塔·马哈马里
6.2. 科尔多瓦的拉巴纳
7. 天文仪器的制作
8. 赞助
8.1. 祖贝达·宾特·阿布·贾法尔·曼苏尔
8.2. Fatima al-Fihriyya
8.3. Dhayfa Khatun
8.4. 赫尔勒姆·苏丹
9. 统治者和政治领袖
9.1. Sitt al-Mulk
9.2. 沙贾拉特·杜尔
9.3. 苏丹娜·拉齐亚
9.4. 扎里亚的阿米娜
9.5. 奥斯曼妇女
10. 结论
11. 致谢
12. 参考文献
1.1 引言
虽然已有多项研究对穆斯林妇女在伊斯兰古典文明的各个领域(如圣训传承、法学(教法)、文学和教育)所做的贡献进行了调查,但迄今为止,很少有资料提及妇女在伊斯兰传统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零星地提到了一些著名的妇女,她们在推动科学发展以及建立慈善、教育和宗教机构方面发挥了作用。例如,祖贝达-宾特-贾法尔-曼苏尔(Zubayda bint Ja'far al-Mansur)在从巴格达到麦加的朝圣路线上开创了一个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即挖掘水井和建造服务站;苏泰塔(Sutayta)是一位数学家,也是法庭上的专家证人、Dhayfa Khatun 擅长管理和政治,Fatima al-Fihriyya 在摩洛哥非斯创建了 Qarawiyin 清真寺(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工程师 Al-'Ijlia 在阿勒颇制造了星盘。
图 1:一幅著名的希帕提娅签名素描,作为插页收录于埃尔伯特·哈伯德 (Elbert Hubbard) 的小册子《名师之家小小旅程》(1908 年第 23 卷第 4 期) 中。
鉴于有关这些妇女的信息很少,而性别和妇女问题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本报告介绍了目前已知的有关这些妇女生活和工作的信息。我们的目的有二:一是介绍现有信息,二是启动调查进程,发掘伊斯兰历史上不同时期数百名妇女在不同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发现。
2. 历史学中的妇女:方法论问题
几千年来,许多妇女在她们的社会中留下了印记,改变了历史进程,影响了重要的生活领域。自古以来,女性在诗歌、文学、医学、哲学和数学领域都有杰出表现。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希帕蒂亚(Hypatia,约 370-415 年),她是一位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教师,生活在希腊化时期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并参与了该城的教育团体[1]。
同样,伊斯兰教对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生于公元前 69 年)的看法也很有趣。阿拉伯语资料称她是一位强大而能干的君主,非常爱护埃及。这些资料重点介绍了她的才能,但没有提到她的道德或诱惑力。相反,这些资料侧重于她的学识和管理才能。埃及艳后在阿拉伯语中的形象与希腊罗马文献中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将埃及艳后描述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和充满诱惑的女人[2]。
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妇女就在其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为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伊莎(Aisha bint Abu Bakr)就具有特殊的管理技能。她成为了圣训学、法学、教育家和演说家[3]。还有许多文献提到穆斯林妇女在医学、文学和法学等领域表现出色。这一悠久的传统在现代也得到了传承。例如,萨比哈·戈克森(Sabiha Gökçen,1913-2001 年)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战斗飞行员。她被任命为土耳其航空研究所的首席培训师[4]。
相比之下,我们在经典史书中几乎找不到有关穆斯林妇女贡献的信息。对尚未编辑的手稿的研究可能会带来新的启示。全世界档案馆中约有 500 万份手稿。其中只有约50,000 份经过编辑,而且大部分与科学无关 [5]。这说明研究人员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图 2:1995 年 8 月 30 日发行的土耳其钞票,纪念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和第一位土耳其女飞行员萨比哈·格克琴 (1913-2001):(来源)。 (来源)。
3. 最新学术研究
不过,这种传统倾向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正在发生变化。最近的一些著作努力恢复妇女在伊斯兰历史中的作用。下面介绍两部此类著作。
3.1. Muhaddithat项目
数年来,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博士开展了一项长期的大型项目,挖掘伊斯兰历史上参与圣训传统的数千名妇女的传记。在 Al-Muhaddithat:纳德维博士在《Al-Muhaddithat:伊斯兰教中的女学者》[6]一书中总结了他的 40 卷本传记辞典(阿拉伯语),其中收录了研究和教授圣训的穆斯林妇女。即使在这篇短文中,他也展示了妇女在传承先知教诲方面的核心作用,先知教诲仍然是理解《古兰经》作为生活准则和规范的主要指南。在她们的宗教范围内,妇女经常在主要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上课,为 “知识”四处奔波,传播和评论圣训,发布法特瓦(裁决),等等。一些最负盛名的男性学者依赖并称赞他们的女教师的学术成就。女学者在社会中享有相当大的公共权威,这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Al-Muhaddithat 中回顾的大量信息对于了解妇女在伊斯兰社会中的作用、她们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潜力至关重要。迄今为止,这些信息都非常分散,以至于被 “隐藏”起来。纳德维博士词典中的信息将极大地促进进一步的研究、背景分析和分析[7]。
图 3:从相邻的房间看,阿富汗巴尔赫的妇女们正在聆听谢赫·巴哈丁·维莱德的布道。Jami’ al-Siyar 的微型图,1600 年。MS Hazine 1230,对开本 112a,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来源)。
3.2. 妇女词典
艾莎·阿卜杜拉赫曼·比尤利(Aisha Abdurrahman Bewley)在其著作《伊斯兰教:Aisha Abdurrahman Bewley 出版了《穆斯林妇女传记辞典》: 传记辞典》。这部以词典形式出版的最及时的作品是伊斯兰历史上穆斯林妇女的综合参考资料,时间跨度从伊斯兰历 1 世纪(希吉里以后)到大约伊斯兰历 13 世纪中叶。这些条目表明,在过去的 14 个世纪中,穆斯林妇女作为学者和女商人取得了成功[8]。
作者写道,她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回应经常提出的要求,提供一些有关女学者的资料:
“当我翻阅我的传记参考资料时,我对提到女性的数量之多感到惊讶,从学者到统治者,无论是摄政者还是以自己的权利进行统治的女性,抑或是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女性,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大量的女性代表。考虑到现代人对伊斯兰教妇女的看法,这些资料让我们惊讶地看到,从伊斯兰教诞生之初到现在,妇女在伊斯兰教历史上是多么活跃。”
该词典涵盖了从先知时代到大约 13-19 世纪中叶的时期。(......)通过对词条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穆斯林妇女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家务。她们活跃在许多领域。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这是一个多种角色的问题,所有这些角色都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分门别类的。商业女性仍然是母亲,学者仍然是妻子。女性只是学会了更多地兼顾各种角色,但这正是女性所擅长的,这一点可以从参赛作品中看出。
这些条目是根据多种资料汇编而成的。许多传记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女性,如伊本-萨德的《塔巴卡特》第八卷和萨哈维的《Kitab an-Nisa'》。有时,在其他参考文献的传记中也会提到女性。许多著名学者都提到过他们的老师,其中包括许多女性。伊本-哈贾尔曾向 53 名女性学习,萨哈维曾向 68 名女性学习 ijazas,苏尤提曾向 33 名女性学习--占他的谢赫的四分之一。Abu'l-Faraj al-Isbahani 所著的《Al-Aghani》是歌手的主要资料来源。Umar Rida Kahhala 著的《A'lam an-Nisa'》是一本极好的现代资料,该书共五卷,涉及著名女性,但绝非包罗万象"[9]。
图 4a-b:Dayfa Khatun 于公元 1235-36 年建造的阿勒颇 Firdaws 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两张视图。(来源)。
4. 概况
在伊斯兰文明中,许多女性所取得的成就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开始揭开面纱。哈里发的女性亲属和朝臣们在文学的赞助和培养方面互相竞争。安达卢西亚艾哈迈德王子的女儿阿耶莎擅长韵律和演说;她的演讲引起了科尔多瓦严肃哲学家们的热烈反响;她的图书馆是王国中最好、最完整的图书馆之一。
瓦拉达(西方学术界称她为瓦拉达)是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公主,她的个人魅力并不亚于她的才华,她以精通诗歌和修辞而闻名;她的谈吐以深邃和精彩而著称;在科尔多瓦的学术竞赛中,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创作,她从未输给过所有的竞争对手。
塞维利亚的阿尔·加萨尼亚和萨菲亚也都是杰出的诗人和演说家;萨菲亚的书法优美完美,无与伦比;她的手稿上的华丽插图让当时最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感到绝望。Al-Faisuli 的天才女儿 Miriam 在文学方面的造诣闻名整个安达卢西亚,据说她的讽刺诗的尖刻诙谐和讽刺性无与伦比。
乌姆·萨达因熟悉穆斯林传统而闻名。科尔多瓦的拉巴娜精通精密科学;她的才能足以解决最复杂的几何和代数问题,她对普通文学的广泛了解为她赢得了哈里发哈坎二世私人秘书的重要职位。
在《AI-Fihrist》一书中,伊本-纳迪姆提到了拥有各种技能的女性。其中两位是语法学家--这是一个备受尊重的知识分支,与阿拉伯语的全面应用有关。有一位女学者研究阿拉伯方言,“她的出身在部落中”,还有一位 “熟悉部落传说和口语”。第三位女学者写了一本题为《动词名词的罕见形式和来源》的书。阿布-努瓦斯(Abu Nuwas)等有抱负的诗人经常与沙漠部落在一起,以完善他们的纯阿拉伯语知识。在另一个领域,“以睿智之言著称的女人”阿尔瓦写了一本关于 “布道、道德和智慧”的书。
Al-'Ijliyah bint al-'Ijli al-Asturlabi 从事星盘制作,这是一门具有重要地位的应用科学,她在阿勒颇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并受雇于 Sayf al-Dawlah(回历 333 年/公元前 944 年-公元前 357 年/967 年)的宫廷,Sayf al-Dawlah 是叙利亚北部强大的哈姆丹统治者之一,在公元 10 世纪守卫着拜占庭帝国的边境。
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一位女性参与其中。塔娜(Thana)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一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家中的奴隶。这位名叫伊本·卡尤马(Ibn Qayyuma)的导师似乎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老师,因为他家中的年轻奴隶和他的皇家学生都从中受益。在他送去接受当时著名书法家伊斯哈格-伊本-哈马德(Ishaq ibn Hammad)培训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女孩塔娜(Thana')。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说,他的学生“写出了从未有过的原始计量字体[10]”。
我们现在简要介绍在医学、数学、天文学、乐器制作和赞助方面表现出色的女性,作为未来研究和进一步调查的范例。
图 5:匿名油画肖像,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描绘的是苏莱曼大帝之妻许蕾姆苏丹或罗克塞拉娜(约 1510 年 - 1558 年 4 月 18 日),她因慈善事业和参与从麦加到耶路撒冷再到伊斯坦布尔的几项大型公共建筑工程而闻名。(来源)。
5. 医疗保健
纵观历史,甚至早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就有穆斯林妇女为提高社会和经济生活质量做出重大贡献的例子。她们积极参与管理、教育、宗教法学、医学和卫生事业,因为她们关心人民的事务。伊斯兰教法》(Sharia)要求穆斯林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因此,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探求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崇拜行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妇女可以作为医生行医,为男女患者提供治疗,尤其是在战场上。然而,严格的男女隔离意味着妇女很少或根本不与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接触。因此,穆斯林妇女的医疗保健工作主要由其他妇女负责。以下是一些为医学进步做出贡献的穆斯林妇女的例子。
伊斯兰教第一位护士的称号归功于 Rufayda Bint Saad Al Aslamiyya。但在伊斯兰教早期,还有其他妇女作为护士和行医者被记录在案: Nusayba Bint Kaab Al-Mazeneya,在乌呼德战役(伊斯兰历 625 年)中为战士提供护理服务的穆斯林妇女之一;Umm Sinan Al-Islami(又名 Umm Imara),成为穆斯林后请求先知穆罕默德允许她与战士们一起外出护理伤员,并为口渴的人提供水、 Umm Matawe' Al-Aslamiyya,她在海巴开战后自愿成为军队中的一名护士;Umm Waraqa Bint Hareth,她在巴德尔战役中参与收集《古兰经》并为战士们提供护理服务。
5.1. 鲁费达·阿斯拉米耶
Rufayda bint Sa'ad,又名 Rufayda al-Aslamiyyah,被认为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位护士,生活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在伊斯兰教纪元 624 年 3 月 13 日的巴德尔战役中,她与先知穆罕默德一起护理战争中的伤员和垂死者。
鲁法伊达通过协助她的父亲萨阿德·阿斯拉姆(Saad Al-Aslamy)学习了大部分医学知识,萨阿德·阿斯拉姆是一名医生。鲁法伊达全身心地投入到护理和照顾病人的工作中,并成为了一名治疗专家。在多次战斗中,她都在自己的帐篷里的野战医院里练习技能,因为先知经常命令将所有伤员抬到她的帐篷里,以便她用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进行治疗。
Rufayda 是一位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护士,也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她利用自己的临床技能,培训其他妇女成为护士,从事医疗保健工作。她还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帮助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问题。此外,她还帮助有需要的儿童,照顾孤儿、残疾人和穷人 [11]。
图 6:两名安达卢西亚阿拉伯妇女正在下棋,一名女孩正在弹奏琵琶(国际象棋问题 #19,F18R),出自阿方索十世的《游戏书》(Libro de los Juegos)。这本书是莱昂和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于公元 1251 年至 1282 年间委托编写的。它反映了伊斯兰遗产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存在。它现在收藏在圣洛伦泽德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图书馆。(来源)。
5.2. 希法·宾特·阿卜杜拉
伴侣 Al-Shifa bint Abduallah al-Qurashiyah al-'Adawiyah 在早期穆斯林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她是当时睿智的女性之一。在文盲时代,她是识字的。她参与公共管理,精通医术。她的本名是莱拉,但 "al-Shifa "的意思是 "治愈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她的职业——护士和行医者。希法曾使用一种预防蚂蚁叮咬的治疗方法,先知认可了她的方法,并要求她培训其他穆斯林妇女 [12]。
5.3. 努赛巴·宾特·哈里斯·安萨里
Nusayba bint Harith al-Ansari,又名 Umm 'Atia,负责照顾战场上的伤员,为他们提供水、食物和急救。此外,她还进行割礼[13]。
5.4. 15 世纪土耳其的女外科医生
在早期伊斯兰历史的这些名字之间,还有其他妇女从事医疗和育婴工作,其中很少有记载。不过,只要认真研究历史、医学和文学著作,就一定能获得有关她们的生平和成就的精确数据。
15 世纪,土耳其外科医生 Serefeddin Sabuncuoglu(1385-1468 年)是著名的外科手术手册《Cerrahiyyetu'l-Haniyye》的作者,他毫不犹豫地绘制了妇产科手术的细节图,或描绘了妇女为女病人进行治疗和手术的场景。他还与女外科医生合作,而他在西方的男同事们则对女医士提出异议。
安纳托利亚的女外科医生通常会进行一些妇科手术,如女性生殖器阴蒂肉质增生、女性阴部穿孔、女性阴部出现尖锐湿疣和红色脓疱、子宫穿孔和糜烂、异常分娩以及异常胎儿或胎盘的取出等手术治疗。有趣的是,在《Cerrahiyyetu'l-Haniyye》中,我们发现了显示女外科医生的微型插图。因此可以推测,这些插图反映了早期(15 世纪)女外科医生对小儿神经外科疾病(如胎儿脑积水和大脑积水)的认识。
医学史中对女性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有趣的是,在 Serefeddin Sabuncuoglu 的论文中,我们发现了对女性的开放观点,包括复杂外科领域的女医生[14]。
6. 数学
在数学领域,伊斯兰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女学者的名字,如 10 世纪巴格达的 Amat-Al-Wahid Sutaita Al-Mahamli 和科尔多瓦的 Labana。用科学史的方法进行系统调查,肯定会获得更多有关伊斯兰历史上其他从事数学研究的女学者的信息。我们知道有许多女性从事伊斯兰法学研究。现在,计算和算术与继承计算(fara'idh 和 mawarith)交织在一起,这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专门用于根据伊斯兰法的规则计算继承。
图 7:菲斯卡拉维因清真寺和大学祈祷大厅庭院景观(拍摄日期:1990 年,版权归麻省理工学院阿迦汗视觉档案馆所有)。
6.1. 苏泰塔-马哈马里
苏泰塔生活在 10 世纪下半叶,出身于巴格达的一个教育世家。她的父亲是法官 Abu Abdallah al-Hussein,著有《Kitab fi al-fiqh》、《Salat al-'idayn 》等多部书籍[15]。她的叔叔是一位圣训学家,她的儿子是 Abu-Hussein Mohammed bin Ahmed bin Ismail al-Mahamli 法官,他以判决和才华著称。
苏泰塔得到了包括她父亲在内的多位学者的教导和指导。其他教过她的学者有艾布·哈姆扎·卡西姆、奥马尔·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希米、伊斯梅尔·阿巴斯·瓦尔拉克和阿卜杜勒-阿尔加菲尔·萨拉马·霍姆西。苏塔伊塔因其良好的声誉、道德和谦逊而闻名。伊本·贾瓦兹(Ibn al-Jawzi)、伊本·哈提卜·巴格达迪(Ibn al-Khatib Baghdadi)和伊本·卡蒂尔(Ibn Kathīr )等历史学家都对她赞赏有加 [16]。她去世于伊斯兰历 377 年/公元前 987 年。
苏泰塔并不只擅长一门学科,而是在阿拉伯文学、圣训、法学和数学等多个领域都很出色。据说她精通 hisab(算术)和 fara'idh(成功率计算),这两种实用的数学分支在她所处的时代都很发达。据说她还发明了其他数学家引用过的方程式的解法,其中包括表示代数能力的方程式。虽然这些方程数量很少,但它们表明她的数学技能已超越了简单的计算能力。
6.2. 科尔多瓦的拉巴纳
科尔多瓦的拉巴娜(西班牙,约 10 世纪)是少数几位有名有姓的伊斯兰女数学家之一。据说她精通精密科学,能够解决当时已知的最复杂的几何和代数问题。她对一般文学的广泛了解为她赢得了伊斯兰西班牙倭马亚哈里发哈卡姆二世私人秘书的重要职位。[17].
7. 天文仪器的制作
在天文学及相关领域,历史记录中只有一个名字,即 Al-'Ijliya,她显然是一位星盘制作者。关于她的信息很少,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资料来源提到过她,那就是著名的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的传记作品《Al-Fihrist》。
在第 VII.2 节(关于数学家、工程师、算术家、音乐家、计算器、占星家、仪器、机器和自动装置制造商的信息)中,Ibn al-Nadim 列出了 16 位工程师、工匠和天文仪器及其他机器工匠的名单。Al-'Ijliya 是名单中唯一的女性,伊本-纳迪姆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名单中的几位专家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可能是萨比安人,而其他人可能是基督徒,这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中推断出来。在名单的最后,有两个条目提到了贝托鲁斯的学生 Al-'Ijli al-Usturlabi,"以及他的女儿 Al-'Ijliya,她曾在 Sayf al-Dawla 的宫廷工作;她是贝托鲁斯的学生"(Al-'Ijli al-Usturlabi ghulâm Bitolus; Al-'Ijliya ibnatuhu ma'a Sayf al-Dawla tilmidhat Bitolus)[18]。
Al-'Ijli 和他女儿的名字源自 Banu 'Ijl,该部落是阿拉伯部落 Banu Bakr 的一部分,属于阿德南部落的拉比阿大分支。巴克尔的原住地在阿拉伯中部的奈杰德,但该部落的大部分贝都因人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向北迁徙,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 Al-Jazirah 地区。土耳其南部的迪亚巴克尔城就是以这个部落的名字命名的。Banu 'Ijl,主要是贝都因人,位于 al-Yamama 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边界 [19]。
从伊本·纳迪姆这段虽然过于简短的引文中可以看出,伊本·纳迪姆没有明确指出阿尔·伊吉利耶的名字,但她是一位仪器制造商的女儿,和她的父亲一样,他们是 9-10 世纪盛行的工程师和天文仪器制造商丰富传统中的一员。伊本·纳迪姆在有关 "机器 "的章节中提到了她,但只是在有关天文仪器的章节中。因此,我们不知道 Al-'Ijliya 是否只是这方面的专家。她曾在阿勒颇(公元 944 年至 967 年在位)的 Sayf al-Dawla 宫廷工作,是一位名叫 Bitolus 的人的学生,后者向她传授了专业秘诀。她的父亲和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提到的几位学者都是这位大师的学徒,这位大师似乎是一位著名的星盘制作师。我们不知道她出生在哪里,也不知道她是在阿勒颇还是其他地方学习乐器制作的。在现存的几件伊斯兰星盘中,没有一件以她的名字命名,而且根据现有的古典资料判断,她是唯一一位与仪器制作或工程工作有关的女性。
图 8:法蒂玛·梅尔尼西 (Fatima Mernissi) 所著《被遗忘的伊斯兰女王》的封面,由玛丽·乔·莱克兰 (Mary Jo Lakeland) 从法语译出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 年,精装版)。
8. 赞助
穆斯林妇女在促进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和科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妇女建造了学校、清真寺和医院。以下是这些妇女的一些例子,以及她们对伊斯兰文明的重要影响。
8.1. 祖贝达·宾特·阿布·贾法尔·曼苏尔
哈伦·拉希德(Harun ar-Rashid)的妻子祖贝达·宾特·阿布·贾法尔(Zubayda bint Abu Ja'far)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女人。她是一位慷慨大方的贵妇人。她在不同的城市开发了许多建筑。众所周知,她曾在巴格达至麦加的朝圣路线上开展了一项巨大的工程,在沿途修建了带有水井的服务站。麦加郊区有名的祖拜达泉水至今仍以她的名字命名。她还是艺术和诗歌的赞助人 [20]。
8.2. 法蒂玛·费赫里亚
法蒂玛·费赫里在其社区的文明和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随父亲 Mohamed al-Fihriyya 从突尼斯的 Qayrawan 移居到非斯。她与姐姐一起在一个受过教育的家庭中长大,并学习了伊斯兰教律和圣训。法蒂玛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她用这笔钱为她的社区修建了一座清真寺。Qarawiyyin 清真寺建于公元 859 年,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学生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学习伊斯兰研究、天文学、语言和科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数字就是通过这所大学在欧洲广为人知并被使用的。这是妇女在教育和文明进步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例子[21]。
8.3. Dhayfa Khatun
Dhayfa Khatun 是阿勒颇阿尤布王朝统治者扎希尔·加齐(al-Zahir Ghazi)强有力的妻子,曾在阿勒颇当了六年的王后。她于公元 1186 年出生在阿勒颇。她的父亲是萨拉赫丁·阿尤比的弟弟阿德尔国王,她的哥哥是卡梅尔国王。她嫁给了萨拉赫丁的儿子扎希尔国王。她的儿子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儿子死后,她成为阿勒颇王后,因为她的孙子只有 7 岁。在她 6 年的统治期间,她面临着蒙古人、塞尔柱人、十字军和花剌子模人的威胁。Dhayfa 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女王;她在整个阿勒颇消除了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税收。她偏爱穷人和科学家,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来支持他们。Dhayfa 是一位杰出的建筑赞助人。她建立了大量捐赠基金,用于维护和运营她的慈善基金会[22]。
除了她的政治和社会角色外,Dhayfa 还在阿勒颇资助学习,她在那里创办了两所学校。第一所是 al-Firdaous 学校,专门教授伊斯兰研究和伊斯兰法,特别是沙菲教义。Al-Firdaous 学校靠近阿勒颇的 Bab al-Makam,根据当时的教育体系结构,学校有一名教师、一名伊玛目和二十名学者。其校园由几栋建筑组成,包括学校、学生宿舍和清真寺。第二所学校是汉卡学校,专门从事伊斯兰教法和其他领域的教学。该校位于Mahalat al-Frafera。1242 年,59 岁的 Dhayfa 去世,葬于阿勒颇城堡[23]。
图 9: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 (Shaykh Mohammad Akram Nadwi) 所著的《穆哈迪塔:伊斯兰女学者》(Al-Muhaddithat: The Women Scholars in Islam) 封面(Interface Publications,2007 年)。本书改编自 M. A. 纳德维的多卷传记词典《穆卡迪玛》(Muqaddimah) 或阿拉伯语前言,该词典介绍了学习和教授圣训的穆斯林女性。《穆哈迪塔》中回顾的大量信息对于了解女性在伊斯兰社会中的角色、她们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潜力至关重要。
8.4. 赫尔雷姆·苏丹
Hürrem Sultan,又名 Roxelana,生于 1500 年,父亲是乌克兰人。在亚乌兹苏丹塞利姆统治时期,克里米亚土耳其人突袭乌克兰,她沦为奴隶,并被送入奥斯曼王宫。她是苏莱曼大帝最宠爱的妃子,并成为他的妻子。赫尔勒姆-苏丹生前热心慈善事业,建立了许多机构。这些机构包括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建筑群和 Haseki Külliye 建筑群,后者由清真寺、medrese、学校和 imaret(公共厨房)组成。她还建造了 çifte hamam(男女双浴室)、两所学校和一所妇女医院。除此之外,她还委托在麦加修建了四所学校,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胡勒姆-苏丹于 1558 年 4 月去世,葬于苏莱曼尼耶清真寺的墓地[24]。
9. 统治者和政治领袖
除了前面几节介绍的妇女在伊斯兰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一些穆斯林妇女在伊斯兰文明的不同地区和阶段作为统治者和政治领袖所发挥的作用。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作为伟大建筑和机构赞助人的 Dhayfa Khatun 女王和 Hurrem Sultan 公主。下面,我们将介绍几位在管理和治理方面杰出的女性。
9.1. Sitt al-Mulk
在穆斯林文明中,没有一位掌权的女性拥有哈里发或伊玛目的头衔。哈里发一直是少数男性的专属头衔。不过,虽然没有女性成为过哈里发,但也有女性成为过苏丹和马利卡斯(王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公主 Sitt al-Mulk 就是其中之一。她聪明、谨慎,没有违反伊斯兰社会的任何政治规则和要求,在履行哈里发的几乎所有职能的同时,她还作为摄政王(为了年幼不能执政的侄子)有效地管理了帝国的事务长达数年(1021-1023 年)。她的头衔是 "副苏丹"(Naib as-Sultan)。
Sitt al-Mulk(970-1023 年)是哈里发哈基姆的姐姐。她的父亲阿齐兹(975-996 年)去世后,她在一位堂兄的帮助下试图将哥哥赶下王位,并成为他的儿子和继任者查希尔的摄政王。扎希尔成年后,她作为顾问继续发挥影响力,这从她慷慨解囊就可见一斑。
掌权后,她废除了哈基姆在位时颁布的许多奇怪规定,并努力缓和与拜占庭帝国在阿勒颇控制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但在谈判完成之前,她于 1023 年 2 月 5 日去世,享年52 岁。
9.2. 沙贾拉特·杜尔
沙贾拉特·杜尔(Shajarat al-Durr)是另一位拥有苏丹称号的王后,她于公元 1250 年在开罗掌权。事实上,她曾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带领穆斯林取得胜利,并俘虏了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沙贾拉特-杜尔(Shajarat al-Durr,阿拉伯语名字的意思是“一串珍珠”)的王室名字是al-Malikah Ismat ad-Din Umm-Khalil Shajarat al-Durr。她是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阿尤布(as-Salih Ayyub)的遗孀,在苏丹死后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埃及(1249-1250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穆鲁克时代的穆斯林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认为她具有突厥血统。她于 1250 年 5 月 2 日成为埃及苏丹,标志着阿尤布王朝统治的结束和马穆鲁克时代的开始。她于 1257 年在开罗去世。
在她的一生和政治生涯中,沙贾拉特-杜尔扮演了许多角色,并在她所居住的宫廷系统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曾担任过军事领导人、母亲和苏丹夫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至 1257 年下台。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来自于她在位的那个时期,其中包括埃及和中东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12 世纪 50 年代,埃及的苏丹地位从阿尤布王朝转移到马穆鲁克王朝。法国路易九世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埃及,攻占达米埃塔,并沿着尼罗河前进,马穆鲁克人在曼苏拉阻击了这支军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沙贾拉特-杜尔崛起,重新建立了政治稳定,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掌握了七年的政治权力[25]。
9.3. 苏丹娜·拉齐亚
在穆斯林世界的另一端,几乎与沙贾拉特-杜尔同时代,另一位女性掌权,但这次是在印度。德里苏丹拉齐亚(或拉齐雅)在德里掌权四年(公元 1236-1240 年)。她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登上德里王位的女性。拉齐雅的祖先是 11 世纪来到印度的土耳其裔穆斯林。与习俗相反,她的父亲选择了她而不是她的兄弟们来继承王位。父亲去世后,她被劝说让位给继兄鲁克努丁,但由于反对他的统治,人民要求她在 1236 年成为苏丹王后。
她建立了和平与秩序,鼓励贸易,修建道路,植树造林,开凿水井,支持诗人、画家和音乐家,修建学校和图书馆,在公共场合不戴面纱,穿着男子的外衣和头饰。国家会议经常向人民开放。然而,当她试图消除对印度教臣民的一些歧视时,却树敌颇多。
她的顾问贾马尔·乌丁·亚库特(Jamal Uddin Yaqut,非土耳其血统)妒忌她的重视,她的总督阿尔图尼亚(Altunia)反叛了。拉齐娅的军队被打败,贾马尔战死,拉齐娅被俘,并于 1240 年嫁给了她的征服者。拉齐娅的一个兄弟自立为王,拉齐娅和她的新丈夫在战斗中被打败,双双战死[26]。
16 世纪印度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 Firishta 曾这样描述她: "公主拥有最有能力的国王所需的一切资质,对她的行为进行最严格审查的人也找不出她有什么缺点,只知道她是个女人。在她父亲的时代,她深入参与政府事务,父亲发现她在政治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因此鼓励她这样做。他曾在自己不在时任命她为摄政王(掌权者)。当埃米尔(军事顾问)问他为什么任命自己的女儿担任这样的职务,而不是他的那么多儿子时,他回答说,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们沉迷于美酒、女人、赌博和对风的崇拜(阿谀奉承);因此,他认为政府的重担太重,他们无法承担,而拉齐亚虽然是个女人,却有男人的头脑和心肠,胜过二十个这样的儿子 [27]。
图 10:Muhammad Khayr Ramadhan Yusuf 所著的《Al-Mu’allifat min al-nisa’ wa-mu’allataftuhunna fi al-tarikh al-islami》(贝鲁特:Dar Ibn Hazm,1412 H)的封面。
9.4. 扎里亚的阿米娜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穆斯林文明时期,有几位女性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色。其中就有扎里亚的阿米娜王后。扎里亚王后阿米娜出生于 1533 年左右萨金(国王)扎佐·诺希尔统治时期。她可能是国王的孙女。扎祖阿是众多豪萨城邦之一,在西边的桑海帝国崩溃后,扎祖阿主导了跨撒哈拉贸易。其财富主要来自皮革制品、布匹、可乐、盐、马匹和进口金属的贸易。
16 岁时,阿米娜成为了她母亲——图伦库的巴克瓦(Bakwa of Turunku)——扎祖阿王后的继承人(Magajiya)。有了这个头衔,阿米娜就有责任管理城市中的一个选区,并每天与其他官员举行会议。虽然母亲在位期间以和平与繁荣著称,但阿米娜也选择向战士们学习军事技能。
1566 年左右,巴克瓦女王去世,扎祖阿的统治权传给了她的弟弟卡拉玛。此时,阿米娜成为扎祖阿骑兵中的佼佼者。她的军事成就为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卡拉玛统治扎祖阿十年后去世,阿米娜成为扎祖阿女王。
她上台三个月后就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军事远征,一直战斗到去世。在她长达 34 年的统治期间,她将 Zazzua 的领土扩张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不过,她的主要重点不是吞并邻国的土地,而是迫使当地统治者接受附庸地位,并允许豪萨商人安全通行。
她的功劳在于推广了土城墙防御工事,这种工事从此成为豪萨城邦的特色。她下令在她建立的每个军营周围修建防御墙。后来,这些防护墙内逐渐形成了城镇,其中许多城镇现在仍然存在。这些城墙被称为“ganuwar Amina”(阿米娜城墙)[28]。
图 11:弗洛伊德·库珀 (Floyd Cooper) 绘制的扎里亚女王阿米娜 (Amina) 画像。
9.5. 奥斯曼妇女
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将介绍奥斯曼妇女,这是一个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16 和 17 世纪,后宫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9]。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后宫是政府的行政中心,只由女性管理[30]。在这一研究领域,系统的调查将取得丰硕的成果。
除上述专业和社会角色外,其他领域也有穆斯林妇女的贡献。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认真调查将大大增进我们对她们的贡献的了解。在化学领域,历史资料引用了Maryam Al-Zinyani 的名字。一些学者认为 Maryam Al-Zinyani 就是 Maryam bint Abdullah al-Hawary,她于公元 758 年在盖拉湾去世。除了写诗,玛丽亚姆还精通化学[31]。
10. 结论
穆斯林妇女与男子一起参与了伊斯兰文化和文明的建设,在诗歌、文学和艺术方面表现出色。此外,穆斯林妇女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和保健专业方面也做出了切实贡献。然而,对穆斯林妇女在科学、技术、医学和管理进步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却很难有据可查,因为这方面的记载寥寥无几。对尚未编辑的手稿的研究可能会带来新的启示。全世界档案馆中约有 500 万份手稿。其中只有约 5 万份经过编辑,而且大部分与科学无关。编辑相关手稿确实是发现穆斯林妇女在科学和文明中的作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11. 致谢
这项工作的完成离不开许多同事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 Mohammed Abattouy 教授、Mehrunisha Suleman 博士、Nabila Dawood 教授、Mohammed Kujja、Suhair Al-Qurashi 博士、Rim Turkmani 博士、Arwa Abde-Aal、Margaret Morris 和 Sundoss Al-Hassani。
原文链接: https://muslimheritage.com/womens-contribution-to-classical-islamic-civilisation-science-medicine-and-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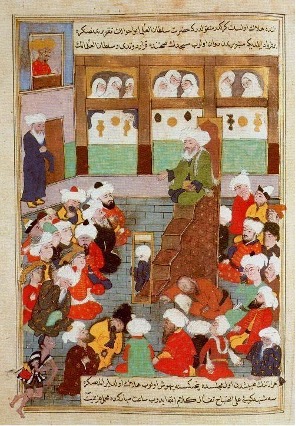
妇女对伊斯兰古典文明的贡献: 科学、医学和政治